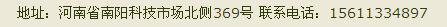湖南大学张俊教授华夏宗教传统与
华夏宗教:传统与赓续
张俊
[作者简介]张俊,年、年、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分别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年从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年被陕西师范大学评聘为教授;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宗教与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宗教学、美学与比较哲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古典美学的复兴——巴尔塔萨神学美学的美学史意义》《德福配享与信仰》等。
摘要
中国自古便存在一个基本宗教信仰传统。然而,近一百多年来,由于受到西方宗教观念的影响,以及国势衰微造成的文化自卑心理作祟,使得国人的基本信仰传统被遮蔽,“中国无宗教”“中国人无信仰”等谬说大行其道。事实上,在传统中国社会,宗教因素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华文化无论雅俗皆受其影响。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几乎看不到没有信仰的人,就算有少数人自认不信鬼神,却也罕见他们公然反对敬天祭祖与崇拜圣贤。华夏民族的基本信仰体系形成于商周时期,可以简称为“华夏宗教”。儒家占据国家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后,成为华夏宗教的担纲者。华夏宗教以祭祀为中心,祭天地、祭鬼神、祭祖先、祭圣贤、祭日月星辰、祭山川风雷,这些活动支撑起华夏民族的信仰,也支撑起了华夏文明。所以,以祭礼为中心(非以崇拜对象为中心)的华夏宗教是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组成部分。礼乐文化,固然有其人文化、道德化、理性化的一面,但其根基仍然是一种宗教祭祀文化。华夏宗教除了国家祀典认可的祭祀外,还有无数处于灰色地带的神祇崇拜弥漫于地方社会的公共祭祀与私人祭祀活动中。华夏宗教兼顾国家宗教和民间宗教,拥有一个以“天命”(天道)为其最高信仰的多元神祇体系,天、神、人、鬼乃至妖魅皆可成为祭祀对象。华夏宗教崇尚血祭,因此区别于崇尚素祭的其他中国宗教。华夏宗教是一种相对于“制度宗教”的“普化宗教”,其神学、仪式、组织都高度依附于世俗宗法社会,与世俗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高度融合。华夏宗教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信仰。其他宗教,都只能在中国人的信仰领域充当这个宗教传统的结构性补充,而且或多或少必须以其为信仰基础。儒家退出国家官僚与文教体系后,华夏宗教自然衰落。恢复华夏宗教的民族信仰正统地位,最重要的意义或许在于以其“普化宗教”的内在属性涵化规约各种“制度性宗教”,避免其成为高度竞争性、排他性的宗教组织力量甚至社会政治力量。
关键词
华夏宗教儒教基本信仰祭祀普化宗教
引言
追溯人类文明的起源,无论是传世文献材料,还是考古文物材料,抑或是人类学田野考察材料,基本都指向同一种文化:巫文化。在巫文化这一人类文明母体中,孕育出了各种自然、社会的知识与精神的信仰,从而形成不同的文明形态。其中,从巫教中演变发展而来的各种宗教信仰,往往成为文明形态区分最本质性的精神内核。
华夏文明作为悠久历史古国的文明,自成一套知识、价值与信仰系统。它之所以屹立世界东方数千年而不倒,是因为有其基本的宗教信仰、价值体系做基础。然而,近一百多年来,由于受到西方宗教观、无神论观念的影响,华夏宗教作为中国人的基本信仰传统这一事实被遮蔽,以致“中国无宗教”“中国人无信仰”等谬说大行其道。这种误解,不仅影响学术判断、误导民众,引起某些外国人或信教者对国人的精神歧视;而且也误导国家对民族、宗教、文化诸领域的决策,削弱国人对华夏民族的身份认同,造成严重的社会及文化后果。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为华夏民族的基本宗教信仰及其价值体系正名。
一“中国无宗教”说何以流行
近代以来,受西方殖民主义宗教观的影响,加之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对文化自信的打击,中国固有的道教和其他民间宗教逐渐被知识阶层视为愚昧迷信加以抛弃。于是,“中国无宗教”在民国年间逐渐成为显论。当然,这种观点还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但是,由于此观点出于一神教判教护教的意图,在20世纪以前并未被儒家为主流的士大夫阶层所接受(甚至也未被众多新教传教士所接受)。而民国知识界的观念之所以发生转变,主要与西方科学主义带来的中西文化之争有关。近代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制度落后于西方,往往被知识界归咎为中国文化的落后,尤其是理性精神的缺乏。所以,在文化自卑心理驱使下,急于想摆脱愚昧形象带来的耻辱感,“通过去宗教来确立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于是,“中国无宗教”的观点开始在知识界流行。
“中国无宗教”被20世纪的知识分子广泛接受,影响深远,甚至影响到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如果说在明清天主教传教士那里,“中国无宗教”还只是一种武断的或居心叵测的判教论断的话,那么,到了民国知识界,这个论断已成为一个思想学术议题了。例如,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的演讲中就提到,凡论宗教一定要有教义和教会的变迁两大要素,根据这两个要素判断,“中国土产里既没有宗教,那么着中国宗教史,主要的部分只是外来的宗教了。外来宗教是佛教、摩尼教、基督教、最初的景教,后来的耶稣教、天主教等”。可以看出,梁启超的宗教观是以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为标准的。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学术界颇有代表性,甚至连以儒家安身立命的梁漱溟、钱穆等也都接受了这一判断。梁漱溟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写道:“世界上宗教最微弱的地方就是中国,最淡于宗教的人是中国人……中国偶有宗教多出于低等动机,其高等动机不成功宗教而别走一路。晚年钱穆在《略论中国宗教》中也说:“宗教为西方文化体系中重要一项目。中国文化中,则不自产宗教。凡属宗教,皆外来,并仅占次要地位。”“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之大体系中无宗教,佛教东来始有之,然不占重要地位。又久而中国化,其宗教之意味遂亦变。”
这种“中国无宗教”学术论断的背后,潜在地是受西方一神论主导的宗教观。虽然此观念早已成为比较宗教学批判的对象,但却丝毫不妨碍它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流行。时至今日,一些学者仍然有意无意地秉持这种宗教观。例如,李泽厚就坚持认为,中国本土没有形成非常明确的宗教传统。在他看来,宗教的核心特征必然包含主客分明、神人分离的“两个世界”,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中没有形成一个与现实生活世界对立的超验世界,其源头是人神不分的巫的传统,是“一个世界”的传统。他认为,西方文明经由“巫”的脱魅走向了宗教和科学,中华文明虽然也有“巫的理性化”努力,却没能最终摆脱巫文化,“巫”纔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意义的‘宗教’,只有经由‘巫的理性化’所形成的人循自然规律而行,自己主宰命运而以‘仁’为根本归属的‘礼教’。”由此,他得出儒家“礼教”纔是中国人的“宗教”的结论。虽然他不认为儒学是宗教,但也不否认儒学包含着敬天法祖的信仰,具有替代宗教的功能,扮演着准宗教的角色;同时,他也承认,儒家对其他宗教和神灵的信仰有极大的包容性。在他看来,这种包容性是上古巫术活动中的多神信仰语境塑造的。这种源自巫文化的多神论,不仅保留在儒家和本土民间信仰中,甚至也渗入到外来宗教中:“中国民间宗教大都是‘体巫而形释’,佛教和模仿佛教的道教实际仍是‘巫’的特质:崇拜对象多元,讲求现实效用,通过念经做法事,使此间人际去灾免祸保平安。”
“中国无宗教”的观点在思想文化界已流行百余年,所造成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导致中国本土固有的传统宗教和儒教被排除在“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兰教)之外,儒教不再具有宗教地位;而传统宗教则被划入民间信仰,常常与迷信混为一谈,不仅得不到政策支持,反而经常处于随时被取缔的灰色地带。二是思想文化界“中国无宗教”的学术见解在民间以讹传讹,变成“中国人无信仰”的成见并广为流布;在当今几乎所有的社会族群都有宗教信仰的情势下,唯独中国人“没有”(即便有,也是“迷信”),这就为其他国族尤其是西方人在道德上贬低中国人的精神文化提供了口实。
二学术界对“中国无宗教”说的批判
对于“中国无宗教”的说法,学术界历来就有不同声音。在19世纪早期,外国来华的第一个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Morrison,—)所编撰的《华英字典》中,就将中国的儒、释、道“三教”译作“ThethreereligionsinChina”,认为它们是与基督教一样的“宗教”(religions)。19世纪中期,麦都思(W.H.Medhurst,—)、罗存德(W.Lobscheid,—)等传教士编修的英汉词典也沿用了此译法。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大会上,代表中国提交论文参会的赫德兰(I.T.Headland,—)、丁韪良(W.A.P.Martin,—)、凯德林(G.T.Candlin)、颜永京(—)、花之安(E.Faber—)、白汉理(H.Blodgett,—)等传教士也都无一例外地肯定了中国存在宗教,中国人有宗教心(信仰)。所以,“中国无宗教”的论调,在新教传教士那里是未被普遍接受的,尽管他们中的多数人基于基督教中心主义的判教立场,对近代儒教、道教、佛教的评价较低。
虽然19世纪中土新教人士已将儒、释、道视为“宗教”,但区别于中古佛教宗派教旨意义的“宗教”。西方学术概念的“宗教”一词传入中国始于清季。作为与西文“religion”的汉词对译,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等人使用了“宗教”一词,后由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引入汉语学界。20世纪初,在日本接触过西方人类学、宗教学的章太炎即明确反对“中国无宗教”的说法。其弟子如鲁迅后来提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周作人也提出“国民的思想全是萨满教的(Shamanistic比称道教更确)”,以反驳当时知识界开始流行的“中国无宗教”观点。这里且不论周氏兄弟对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底色的认识是否允洽,他们驳斥“中国无宗教”说法的同时,不仅没把传统宗教作为中华文明来称颂,反而认为这种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是国民愚昧的原因,这就等于将中国宗教自觉地摆到了相对于“高等宗教”(如基督教)的“低等宗教”“巫术”的位置。所以,表面上他们否定“中国无宗教”的观点,但其实质并未摆脱当时普遍的文化自卑。
在当代新儒家中,也有反对“中国无宗教”的声音。如唐君毅就讲:“世之论者,咸谓中国无宗教,亦不须有宗教。然如宗教精神之特征,唯在信绝对之精神实在,则中国古代实信天为一绝对之精神生命实在。”“绝对之精神实在”虽出自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口,但这明显是哲学化的基督教终极实体观念的翻版,一如黑格尔(G.W.F.Hegel,—)所谓之“绝对精神”。中国人的昊天上帝信仰,可以看作是多神信仰语境中的至上神信仰,但它绝不是一神教哲学语境中那个“绝对之精神实在”,否则,《诗经》中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疑天、怨天甚至詈天的诗句了。就算是后来经过儒家理性化抽象后的义理之天——“天道”“天理”,也与基督教神哲学中的终极实体概念大不相同。中国人信奉的“天道”不是绝对的、超验的。如果按照李泽厚的观点,中国人的终极信仰始终在巫史传统的“一个世界”中,根本就没有所谓“绝对”:“中国是一个世界,西方是两个世界……中国巫史传统没有这种两分观念,纔可能发展出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它追求中庸与度,讲求礼仁并举、阴阳一体、儒法互用、儒道互补、情理和谐,显然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上帝至上、理性至上。”
既然“中国无宗教”是一种谬说,那么,该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固有的宗教传统呢?答案是:首先需要摆脱西方(基督教)中心主义的宗教观。其实,当年的黑格尔已看到了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的差别:“中国的宗教,不是我们所谓的宗教。因为,我们所谓的宗教,是指‘精神’退回到了自身之内,专事想象它自己的主要的性质、它自己的最内在的‘存在’。”加拿大汉学家欧大年(DanielL.Overmyer)也明确讲:“我们不能以西方基督教模式的宗教理解来判断中国人的信仰活动。”只有跳出西方一神教的宗教范式,也许纔能不带偏见地认识中国固有的宗教传统,而不至于将其贬低为“低级信仰”或“迷信”。
在20世纪,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宗教学家比哲学家抢先一步,跨出了这种误导性的宗教知识模式。例如,杨庆堃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写道:
低估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实际上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寺院、祠堂、神坛和拜神的地方。寺院、神坛散落于各处,举目皆是,表明宗教在中国社会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它们是一个社会现实的象征。
其实,在传统中国社会,除了公共祭祀的场所和活动随处可见外,还有大量私人祭祀的场所及宗教信仰活动,如家庙祭祀、扫墓祭奠祖先、私宅中举行的各种禳灾祈福的法事等等。几乎每个家庭都可以算作一个小型的宗教祭祀场所和信仰组织,除了供奉祖先神位,家庭内部还有灶神、财神、门神之类的信仰活动广泛存在。由于宗教因素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中华文化体系中,雅俗文化、大小传统皆受其影响。所以,李亦园认为,“在传统中国普化宗教的影响下,实际上并无绝对的无信仰者存在”。
根据杨庆堃的研究,中国原本就存在着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从周朝到西汉时期,在外来佛教的影响形成和道教作为宗教出现之前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个宗教传统崇拜的核心,是“天”以及众神和祖先。“中国和华夏,在春秋时就有一个大规模的祭祀体系。汉唐时期的儒、道、佛和民间宗教延续了这个祭祀体系,也都擅长祭礼。延至后世,无论是明清庙祭(祠堂祭祖),还是当代墓祭(清明扫墓),都表现出社会性、制度性的特征。”
中国本土固有的这个宗教传统,宗教学界多将其称为“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但是,这两个概念很难突出其作为中华基本宗教的特质,甚至很难与儒、释、道三教划清界限。因为,一方面,儒、释、道都已发展出官方(精英)和民间(大众)两种宗教形态;另一方面,在现实语境中,“民间宗教”常常被用来指称民间新兴教派,“民间信仰”经常被归入不入流的“低级信仰”甚至“迷信”。所以,这两个概念不适于指称中华民族固有的基本宗教信仰。尽管如此,如果使用与这两个概念相对应的英文“PopularReligion”和“PopularBelieving”并无不妥,因为中华基本宗教能够流传数千年而不衰,其定然是深受民众喜欢的信仰方式。早期还有个别学者使用“原始宗教”“巫教”(“萨满教”)等概念,这大概是基于中华本土宗教源自巫觋传统;但是,在宗教学中,这些概念都属低等宗教的范畴,明显不能反映中国这种基本宗教在历史长河中发展蜕变的文化特征。所以,还是称之为“中华基本宗教”(ChinesePrimitiveReligion)或“中华传统宗教”(ChineseTraditionalReligion)比较恰当,也可简称为“华夏宗教”(HuaxiaReligionorChinese-ism)。
三华夏宗教的起源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型国家。因为,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国度,其主体民族汉族本身也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汉族”在历史上更多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种族概念。凡是使用汉字或汉语,接受汉文化及其承载的价值与信仰者,其实都可算作汉族。今天民族志意义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概念及其影响下的民族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汉族从宽泛的文化概念推向了狭义的种族概念。为了避免这种狭义汉族概念影响到学术思想的客观性,这里使用文化意义的“华夏”一词来指称“文化中国”这个广义族群概念,故将“中华基本宗教”简称为“华夏宗教”。唐人孔颖达对此解释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服章礼仪之华美堂皇,是华夏文明的直观体现。服章礼仪背后,正是礼乐文化(信仰文化)的高度发达。而最隆重华丽的服章礼仪,往往出现在华夏民族的祭祀典礼之中,正所谓“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中华文明的基础在礼乐,祭祀是中国礼乐文明最重要的部分,这恰恰就是华夏宗教最核心的内容。祭天地、祭日月星辰、祭山川风雷、祭鬼神、祭祖先圣贤,祭祀礼仪支撑起华夏民族的信仰,也支撑起了整个中华传统礼仪之邦的文明。
以礼乐祭祀为代表形态的华夏宗教文化,主要形成于西周。但礼教并不是华夏宗教的全部内涵,只是在先秦时期发展出的一种高级文化形态(主要为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华夏宗教的源头要早于西周,《礼记·表记》中言:“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而宗教祭祀的系统化,儒家甚至上溯至唐虞之前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关于“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有较为详细的演绎:
及少皥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虽然“绝地天通”最早见之于《尚书》,《山海经》《国语》《墨子》《史记》也有记述,但毕竟“五帝”时代邈远,“重、黎绝地天通”作为历史事件后人无法考证其真伪,只能结合宗教与政治的宏观历史进程推测它在历史上发生过。“绝地天通”本质是上古社会部落兼并过程中,酋邦统治者的一种思想信仰整合手段——需要建立公共祭祀与信仰体系,以替代各自为政的巫术信仰和部落神祇崇拜,从而垄断占卜与祭祀,获得统治的合法性。
在氏族部落社会,族群内部成员一般接受的是相同的图腾信仰与禁忌,通常没有变革信仰体系的内在需要。而在外部,部落联盟首领通过举贤禅让,权杖在不同部落之间流转,也不存在以一个部落的信仰取代其他部落信仰的必要性。所以,“绝地天通”这种宗教革命,只能出现在拥有世袭制和等级制的酋邦。酋邦统治者为了自身统治与子孙世袭特权的合法性,必然要整顿各自为政的部落神灵信仰和巫术活动,废黜不利于己的所谓“淫祀”,尽可能地打击私人崇拜,将各部落原始宗教信仰纳入一个统一的神祇体系中,并安排专门的祭祀官(如“重”这样的祭司家族)负责管理,以保障神灵世界的话语权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为现实政治秩序服务。正是“绝地天通”这一革命,客观上促成了统一的酋邦祭祀体系的产生,为之后华夏宗教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由于缺乏文献材料的支撑,商周以前的华夏宗教面目是非常模糊的,这里只能大致推断它是从“巫教”或“萨满教”脱胎而来。面对此类棘手问题,即使在孔子时代也颇感无奈:“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但是,今人比孔子幸运的是,可以通过对商周之前的大量考古发现来佐证。譬如,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钺、玉璜等,红山文化的玉龙、玉猪龙、玉龟、玉鸟、双熊头三孔玉器、勾云佩、玉璧等,考古学家通常都视之为祀神器或祭祀礼器。其中,玉龙、玉龟、玉鸟、玉熊等物本身就是图腾偶像,部落宗教祭祀崇拜的对象。所以,学术界根据出土文物断定商周以前华夏先民的宗教信仰为巫教,大致是没有问题的。但何时“绝地天通”,实现各部落巫教神祇系统的统一,从而形成华夏宗教的体系雏形,始终是个悬案。这里只能暂时将华夏宗教的形成假设在商周时期。
殷商虽典籍信史稀缺,但随着甲骨卜辞以及大量青铜器、玉器的出土,已能够大致推断其宗教信仰状况。其中,甲骨文作为出土文献,为学术界提供了第一手史料。作为初步成熟的早期汉字,甲骨文首先便是卜官掌握的一种宗教文字,其主要用途是记录殷商王室的占卜活动,故甲骨文又称“卜辞”,或“贞卜文字”。商人笃信鬼神和上帝,迷信占卜,无论是祭祀、战争这样的国家大事,还是以田猎、生育之类的私事,都要鬼神的“启示”来预测、指导。根据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张光直、何炳棣、胡厚宣等学者对甲骨卜辞的研究,殷商时期的主要宗教信仰与祖先崇拜有关,其热情远超过对“上帝”和各种神明的崇拜。胡厚宣发现,卜辞中关于祭祀的部分主要是关于卜祭先祖的,商王室似乎并不直接祭祀上帝。不过,商人相信,其先祖先王死后会上宾于天陪侍上帝(“宾帝”“宾于帝”),他们可以通过祭祀祖先、以祖先为中介来祈祷于上帝。所以,在商人的信仰世界中,上帝的众神之主的“至上神”地位是确定无疑的,上帝之下是日、月、风、云、雷、雨、雹等自然神及商人的祖先神。可见,以上帝(天)、诸神、祖先为主要崇拜对象的中华神祇体系,在殷商时期已经成型。杨庆堃所讲的中华传统宗教的关键组成部分——“祖先崇拜、对天及其自然神的崇拜、占卜和祭祀”,在殷商宗教活动中都能看到。
李天纲认为,华夏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甚至道教的一个显著不同,是采用“血祭”。“血祭”的传统应该与巫教有关系,但并无坚实的证据。20世纪以来,殷墟出土的大量祭祀卜辞和墓葬表明,商人在宗教祭祀活动中不仅有大规模的“牺牲”(或燎、或瘗、或沉),甚至有极其残忍的人殉。这种血祭传统在商周鼎革之后,也被周人继承,并被纳入礼教(如“太牢”“少牢”“荐新”诸礼)流传下来,直到今日。汉字的“祭”字,其书写方式本身就是血祭的反映,《说文解字》讲:“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血食祭祀虽然不是华夏宗教独有的现象,但却是华夏宗教几千年不变的传统。在中国,这一祭祀传统足以使其与崇尚“素祭”的大多数“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Religion)区别开来。
《论语·为政》讲:“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三代鼎革,其在礼仪文化方面皆有继承,皆有变革,这原本是情理中的事情。周人也是华夏宗教的奠基者,他们又是如何继承并变革商人的宗教体系的呢?“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王国维讲:“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在政治上,周代殷命,封邦建国,一个相对统一的宗法政治体系被建立起来。为了维护这一政治体系,周初统治者不得不设法统一思想,制定新的典章制度(祀典),于是,制礼作乐成为他们的首要工作。周人奠基的礼乐文化也从根本上成就了华夏文化。按照李泽厚的观点,制礼作乐完成了上古巫史传统的“理性化”,而内“德”外“礼”就是这一理性化完成的标志,它奠定了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根本。虽然李泽厚敏锐地洞见了西周礼乐文化“理性化”对华夏文化的奠基性影响,但却忽略了其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一种祭祀文化。如《汉书·郊祀志上》所讲:
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礼作乐,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咸秩无文。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而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大夫祭门、户、井、灶、中溜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
西周统治者通过以严明的宗法等级制度来掌控天下祭祀,从而获得政权合法性及统治话语权。像之前或之后的所有统一政权一样,他们有强烈的政治需要禁绝不合“礼法”的“淫祀”,同时“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将部落神祇整合到统一的信仰体系中。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为这个信仰体系树立神学的中心,这就是天命信仰。不同于殷人对祖先崇拜的依赖,周人前所未有地强调了昊天上帝至高无上的神学地位,并赋予周天子郊祀祭天的特权。这一神学思想为后世王朝普遍继承。
除此之外,周人以政治统摄宗教的礼制也为后世树立了典范。从此,“朝廷不仅掌握了祭天的垄断支配权,还控制了庙宇的兴建、神职的任命及僧侣的管理”。华夏宗教因此不得不依附于政治,再也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教会组织成为“制度性宗教”,只能附庸于世俗政权及社会成为所谓的“弥漫性宗教”或“普化宗教”(DiffusedReligion)。由于华夏宗教高度依附世俗社会并服务于信众的现实生活,日本学者渡边欣雄甚至在其《汉族的宗教》一书中将华夏宗教称为“民俗宗教”。由于没有独立且有自身利益的教会组织,华夏宗教与社会难以形成张力,更不能与世俗权力竞争,故而它不得不围绕信众的尘世生活诉求展开其信仰活动。所以,在现代宗教学以“制度性宗教”为范型的宗教类型图谱中,作为本土基础信仰的华夏宗教的面目注定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难怪“中国无宗教”的说法会广泛流行了。
周人奠定的华夏宗教传统,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祀典——祭祀礼乐制度的地位被前所未有地突出。周人对祀典(本质是体现宗法等级的礼仪制度)的强调,远超过对神明本身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iogko.com/wazlyy/10089.html